[转贴]如何评价《杜凤治日记》?
回答1:
我是先看的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各位可以直接去看白话文版,名为《我在大清官场30年》),张进士出身,宦海经历贯穿道、咸、同,起步就是36岁出任山西朔平知府,历任多省的按察使、布政使等二三品要职,换算成现在,大致是厅局级到副部级之间,可称一方大员。即便如此,书中也是多处流露出“官太小,没升上去很痛苦”、“立功立德立言无一做到”,而本文作者杜凤治,举人出身,一生中最高的官是正五品广东罗定知州,还是署理(代理),可以说,张的起步,就是杜最高点都没够着的地方。
杜凤治30岁中举人,但53岁才补上实缺,为此在京城等了十几年,期间只能干点兼职(教书先生或幕客),家人在老家浙江过的甚苦,又逢太平军席卷浙江,家中多人逃难中病死、失踪,而杜丝毫没有办法,哪怕几年后境遇稍好,把部分家人接来,但依旧拮据,以至于席子蚊帐都买不起。哪怕后来靠着加捐外加运气不错(排在他前面的丁忧了)得了个广东广宁知县的实缺(当时广东就是全国经济首屈一指的地区,广宁又可算其中的优缺),杜凤治依然没办法放宽心:
首先,清朝对官员赴任一分不给,也不安排交通工具,全靠官员自行解决;
其次,到了之后得拜会督、抚、藩、臬等上司,以及在省城的幕友、其他官员,这里面的拜会打点自然也少不了;
第三,清朝给每县的编制极少,如衙役、佐杂,一般只有几人到几十人不等的编制,而实际人数很可能百倍于此,多出来的人工资也是知县管;
第四,偌大一个县,单靠知县一人自是忙不过来的,何况很多知县都是读四书五经出身,根本不懂具体事务,于是就需要聘请师爷,其中钱谷(管账)和刑名(管司法)的师爷是必须,其他还包括收粮(征收)、阅文(乡试)等。师爷的工资自然不菲,若是县内事务繁忙,所需师爷更多,如杜凤治任南海知县(广东首府首县)时,共聘7名师爷负责钱谷和刑名,每年工资就6000两,而彼时杜凤治自己的工资只有1575两(还没法保证全额到手)
凡此种种,杜凤治只能去借高利贷,他上任前共计借了8180两银子,其中很多还是“对扣”(借款一半扣为利息,即现在的“砍头息”);且杜凤治上任没多久,就卷进了上司之间的斗争里,彼时两广总督、按察使与巡抚、布政使之间势同水火,杜被当成失败一方的党羽,被迫调署去了收入较少的四会任职。他一度在日记里哀嚎“若回头有路,三百水田,绝不敢干这九幽十八地狱营生!”然而,由于赴任时债务没还完,在广宁又卷进派系斗争而亏累,除了硬着头皮干下去,他也没别的选择。
之后几年,老杜凭借自己的才具,以及逐渐积攒的经验,仕途开始顺利起来,后面两度出任广东首县南海知县,也还清债务,有了积蓄,最后在光绪六年辞官归里时,保守估计,带回老家的财产作价45000两白银。
但要说一点气不受,那也是不可能的。如光绪三年,他本来和上司谈妥卸任南海知县后升补罗定知州(正式的),结果转过年来,佛冈出了乱子,督、抚、布政使都要他去善后,杜根本不想去这么个苦差不说,所谓的善后,上面根本不拨一分款,全得自己赔垫。杜本想直接辞职,但被妻子劝住,“儿子均幼小,不能不忍气、过几年再说”,于是杜只能赴任。日记里对上司的不满甚至咬牙切齿比比皆是,如对按察使梅启照、张瀛,盐运使钟谦钧等,用破口大骂来形容措辞都算文雅了,如形容张不顾官场实际挑剔为难是“屙屎自吃”“殆非人类”,钟谄媚上司的做派是“连P眼都是快活的”“不当人视之”,寥寥几笔,言语间刻毒尽显。当然,尽管私下里恨得牙根痒痒,表面功夫都是做得很好的,杜在日记里记录每年光给上司们打点,就要用去两三万两。
要说这部日记里面给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大致是以下几点。
一、州县官可以说是极其难干,但也极容易获利的。作为承上启下的存在,州县官除了辛苦之外相当受气,杜就记下了官员们的一句顺口溜“前生不善,今生州县;前生作恶,州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州县官公务繁忙(下乡催粮、案件初审、主持乡试等)不说,还要协调处理好和上司以及本地士绅之间的关系,上司之间、上司和地方乡绅间也往往有冲突矛盾,此时州县官可以说是夹心饼干两头堵,两边都要调和、都不能得罪。
另一点是清代财政实际上已经形成地方州县官“大包干”制度,说白了就是只要按时往上缴纳钱粮就行,上面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弄出来的,别闹出大乱子就行,能者多捞,差者滚蛋(规定是上缴税额不足九成就冻结升迁,不足五成就地免职)。
当然钱粮不是那么好征的(参见现在为了收医保,都要三催四请、人头摊派,何况基层动员力没那么强的晚清),虽然各乡都有粮站和驻派委员,还是会出现州县官不亲自去,就收不上来钱的情况。所以杜凤治日记里没少记载下乡催征钱粮的事,往往一下乡就是一两个月。
由于日常开支(家庭生活、上司馈赠等)和突发性开支(视察委员程仪、衙署维修等)都无法避免,广东又经济发达,物价高昂,州县官必须比其他省的官捞更多的钱才能维持住资金链,导致稍有不慎,就会亏累。杜凤治日记里就记载了多位因任苦缺知县而亏累不堪的官员,哪怕是优缺如首县南海,照样有人会亏损,如杜的后任张琮,因到任就遇到上司丧事、到任等多件大事,又没和巡抚张兆栋搞好关系,结果在刚垫完开支,还没时间弥补收入的节骨眼被撤职,日记记载张自己说这一任“即亏八万两”,窘迫到连挑夫钱都拿不出了。然而,满载而归者亦大有人在,如同为张姓的张庆嶸,在“累缺”东莞知县一任就捞走了五万两银米羡余。
这其中的门道自然很多,如前任离职前往往“放炮”收粮收钱(比如本来要交5000,现在交4000就行,限期几天,过时不候),或减收过户契税(标准6.5%),杜离任南海前降到2.4%,过户金额54万两,净赚12960两,前任赓飏直接降到1.8%。
因为前任这样“放炮”、减税,把当年应征钱粮收走一大半,导致继任者往往不仅收不上来钱,还要自己垫出大笔开支去办公务。
当然,也不是说后任们都是小白兔,如同治十三年,番禺知县彭君谷丁忧,任上亏空甚多,布政使表示谁愿弥补亏空就让谁署理,这是当时官场通行的潜规则。朱昌言表示愿承担2.8万两,结果上任之后翻脸不认人,此事又不便端上桌面讨论,结果两人在上司面前多次大闹,但朱从头至尾没有掏钱。凡此种种,导致前后任之间经常矛盾尖锐,甚至在上司面前公然互殴。
二、酷刑折磨、法外杀人已经是常态,徇私枉法更不必提。杜已经算是相对手轻的,但日记里也有多处提到把犯人用站笼弄死、枷死等,也记录了其他知县的相同做法,甚至有知县直接活埋罪犯,至于徇私收钱,更是不胜枚举,连杜自己都感慨“衙门官司不可沾着,一沾即可破家”
三、晚清官场“无官不贪”。上到两广总督(瑞麟贪腐在京城都是挂的上号的),下到佐杂、门房,可以说是层层扒皮维持生活。特别是杜的日记里还描写了多位学政、主考“要钱不要脸”的行径,如同治十二年乡试副主考周冠,前后捞走近万金,光绪元年乡试副主考朱琛也获利七千余金。
特别是周冠,由于其吃相太过难看、求索过于繁重,在其路过清远时,知县、周的旧交郑晓如直接翻脸,一分不给,反倒赠诗一首:“岭南官味如鸡肋,海上仙槎有风声;笑我忝为东道主,廉泉难慰故人情”。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要告随你,正不想干!”周冠大怒,却也无可奈何。连这些“清贵官”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当然,不贪的官也确实干不下去。
第四,是官民之间的冲突已经尖锐至极。一方面,是许多村庄不仅“向不完粮”,时间长的甚至从道光年间就没交过钱粮,并且敢于结寨抗拒官兵,如果官军打不进村,一分钱收不到不说,其他村更是纷纷效仿;如果想征收上来钱粮,非狠辣手段不可,如杜在南海的前任陈善圻,因辣手催征过程中闹出许多人命,在当地得了个“陈三皮”的绰号,即刮尽地皮、剥光人皮、不要脸皮。
另一方面,由于钱粮难收,收上来的也经常被官吏私分,久而久之上面发现收不上来钱,就会派官兵出动“清乡”。没错,顾名思义,和日伪时期干的事情非常相似,杀人放火,开炮轰村都是常事。
如前文所说,打不进去就拿不到钱,而只要打进去了,由于百姓久已欠粮,根本不知该交多少,只是被官府打服了才交钱。因此,官府不仅能收回钱粮,还能罚款以补充军火兵饷,更能漫天要价,从中大发其财。其中的残忍手段,自不必提,连杜都直言几位总兵“不过冤杀许多平人为自己立功,不论真假,愈杀的多愈妙”(其中有的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后来投诚,类似《水浒传》)
PS:原著确实太大部头(原件40本,几百万字,横跨十几年,哪怕后来的点注本也是10大本,而且不便宜),可以直接看邱捷教授的《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经评论区提醒,去搜了一下在网上对周冠(字鼎卿)的描述,看得我愣了半晌,反复确认和杜凤治笔下描述的是同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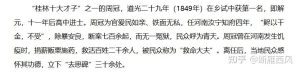
千金不受 因为之前万金捞足了是吧
注意,这是中国纪检监察报上的文字,不是什么野鸡网页;而老杜笔下的周冠干了些什么呢?
1.规矩是沿途接待州县官摆酒接风,周“不受酒席,要折银”,还让给他准备蟒袍朝衣啥的,做个类比,约等于《人民的名义》里肖钢玉找刘新建卖那两条中华烟
2.惯例是每日每位主考12元伙食费,周要17两,当时大致1元=0.72两,等于直接翻倍,最后给了10两
3.一般来说,同年、同乡或有旧交的会多给,周为了多捞钱,滥认同年,类似于《儒林外史》里张乡绅和范进攀关系的举动;特别是南海、番禺为广东当时两首县,彼时后者知县胡鉴是周冠真·同年,加送了200两,于是周派人找老杜也要200两,把老杜气得半死,直接回他说南海已按规矩送完了
凡此种种,按老杜日记原话是“无日不小轿进城张罗拉扯,声名大坏,秽德彰闻”、“无日不拜客,无日不宴会,无日不到河下饮花酒,要钱不要名”,可以说讲的很难听了;虽然老杜笔下描写了多名学政、主考既不清不廉也不自尊自重,但这里面对周冠的评价可以说是最差的
补充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前文提到的光绪元年副主考朱琛,临走前表示周冠和他讲过上次临行前正副主考在科场厅每人得了2500两“程仪”,这次也必须给够,不然不走;最后是两县和抚台打过招呼,给到2000两才算把人打发走
看到今天大同案二审宣判了,有点感慨,想起老杜曾经判过的一个案子,贴出来供大家一览
案件本身也不复杂,大致就是奸夫淫妇正苟且时,正主回来抓个正着,奸夫逃跑的时候落进河里淹死;老杜直接上刑,掌掴女方4次拿到口供,发现女方不是第1次这么干了,甚至之前还离家出走过一个月,后来发现男方干小生意赚的钱还不少,就又回来了,男方居然当啥事儿都没发生过
老杜看出男方还是对女方有所留恋,于是直接走律例判女方“官卖”,并且对男方说,官府衙役“均知汝有几个钱,尽可以破汝家”,但人家给你办事也出了力,“小小茶资不能不应酬一二”,但不用多给,如果有官差勒索过度,“竟来大堂大声喊冤可也”。前面已经叙述过,杜自己都说,对普通百姓而言,“衙门官司不可沾着,一沾即可破家”,作为知县能对草民照顾到这个份上,已经算不容易了。
回答2:
非常有意思的书。杜本人50多岁当官,一辈子干州县官直到70岁,不是顶好的官,但也不是昏官,算是当时合格的士大夫。
一方面杜是能体谅普通人的。他感慨普通人千万不要打官司,无论有理还是没理,一旦沾上官司就是倾家荡产,差役、佐杂、宗族、讼师、保人都盯着你,要把你榨干,到最后想不打官司都不行。所以他有时息讼不仅是出于惯例,也是为当事人考虑。他处理女性被奸污的案子,一般都是否认奸污情节、然后用其他罪名把嫌犯重处,因为女性沾上奸污之名难以做人,奸污案子缠讼时间又长,他这样既能保全女性名节,又可以息讼。
另一方面杜是官僚群体的一员,维护统治、官官相护的事情更多。他在广宁知县任上的时遇到罗亚水案,就选择给前任捂盖子。罗案是在他的前前任发生,罗亚水杀了同族三人,宗族出面赔钱了事,所以死者家属不上告、认了罗亚水溺水自杀(实际是没死,跑了),他的前任也不想详查,糊弄过去了。到杜时,死者家属又来告状,杜一看就知道是赔偿没到位,但他也不想得罪两个前任,就拖过去了。杜离任后,后任也是同样的做法。这个案子最后闹到省里,州县官员商量后的处理意见是“非亚水死不可,惟饿死与病死等耳”,后来杜没再记载这件事,大概率就是罗亚水死了,不了了之。
另外,晚清人口迅速增加给基层治理带来的压力被中下层地方官不约而同的感受到了。杜是州县官,他反复说“广东人何其多也”、“游手好闲之人太多,思乱可以有为之人亦不少,皆散处未萃耳。设有仗义疏财、辍耕叹息之奸雄出,攘臂一呼,势必人如归市,十万众可立致也”。比他稍早的张集馨是历任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福建的中上层地方官,他的《张集馨日记》也一直说四川、福建难治理是因为人太多太多。
回答3:
我建议所有大学生都看看,包括刚走向社会的青年,
还有家庭主妇、宅男、主观觉得自己幼稚不成熟的朋友,都可以看看。
这本书最牛的方面是非常细腻刻画出真实世界,
而上述人群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活动经验,看完这本书,读者能感知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要素。
杜凤治,清朝同光年间的县官,考上举人后,依然贫困潦倒,在北京给人当幕僚为生,只能勉强糊口,老家妻女都顾不上,那时正是太平天国在江浙盘踞,杜家被战火波及,苦不堪言,杜凤治女儿和妻子先后去世,杜在北京捶足顿胸,肝肠寸断。
后来好不容易轮上广东县官,已经四五十岁了,还需要自己筹措路费,没钱只能去借,京城专门有人给上任官员借贷,高利贷,利息惊人。杜凤治借了一千多两,花了十几天,从天津出发,坐轮船中转上海,再到香港,最后到达广州,只为省钱。
杜凤治在广东各地任职十几年,他精力过人,每天处理各类大事琐事,还能抽出时间写日记,起初经济拮据,为了节约纸张,日记中写的字很小,后来渐渐宽裕,下笔才舒展一些。
日记中记录了很多东西,包括和同僚的关系、议论上级、晚清官场的陋习、怎样治理一方百姓,对洋人洋货的描写……
我们看的历史类书籍,绝大部分都是宏大叙事,几几年发生什么事件啦,朝廷怎么样啦,皇帝任免谁啦,但这种从基层官员的视角,去看当时世界的资料,可以说非常珍贵。对于普通人,看多了宏大叙事,再看看细微之处,感触颇多。
《杜凤治日记》原始材料,读起来可能有点难度,建议看这本《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豆瓣评分8.8,微信读书推荐值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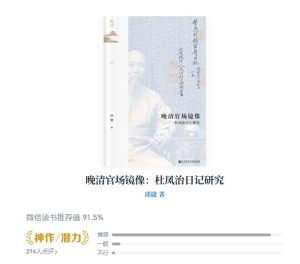

回答4:
晚清的广东治理体系,主打一个黑社会帮闲体系,
衙门下乡收税,火枪开路,烧屋伤人为辅,打得过村庄的,就收得到税,打不过的就收不到税。
如柳岗绅耆不将陈同交出就开炮轰村。杜凤治认为轰村的办法不行,建议朱用孚先焚烧“匪村”新寮,“以服人心,以吓匪人,而完粮亦心中生畏”,向绅民表明抗粮者烧屋之说并非空言恐吓。
广东地方乡绅,一边担着功名,一边半公开的走私,时而官,时而匪。
粤督,对下面百姓,以高压为主,杀人威慑,既捕既杀,以此震撼平民百姓。
但是某个县丞下乡缉捕走私盗贼,反倒被走私强盗挂竿示众。最后被人说破是背后站着某官绅撑着走私。
县丞沈茂霖(雨香)作为委员在廉州查洋药、收军饷,带领差、勇捉拿走私鸦片的团伙,私枭首先开炮,然后“将雨香及满船人均擒去,书差、丁勇人等俱破膛,雨香则悬之高竿,欲其晒死。正在将死未死,县官往求,那边亦有绅士向其说,如官不死尚可不奏,尔等亦轻,倘一死,事闹大矣。那边不肯,活活死在竿上”。[40]此事既说明鸦片私枭的猖獗凶残,也透露了私枭团伙同官、绅都有勾结,平日很可能通过贿赂造成一个“猫鼠互利”的局面,沈茂霖因为太认真却缺乏实力而送了命。
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麻烦。
杜凤治,做个破知县,找七八个大小师爷慕席,结果广州将军,布政使,按察使,粮道,都有推荐。
客案席姚诗南(振伯),将军所荐,每年脩千二百金;刑席戴尧恩(云墀),臬台荐,脩千二百金;刑席李政卿,粮道荐,脩千二百元;刑席但鸿恩,原广宁幕客,脩千二百元;刑席吴存履(爱亭),肇庆府幕客吴桢荐,脩六百元;钱谷孟星航,杜自请,脩千元;钱谷陈文江,藩台荐,脩千元。教读兼书禀李紫珊,书禀诸青田、陆芷言、黎丹卿,征比陈商盘、陈韶九、章梿(朱笔墨)、陈森林,又涂厚山之
主打的就是一个人情世故含金量。
人世情故遍布广省上下,
贿赂都不见贿赂了,那就程序办事,
你要某个职位或者差事,先得给上司送钱,送的钱,才能下面打秋风,
这叫,贷款上班。
就这还得排队,
晚清官场,本来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清朝中期,什么宗室缺,满缺,蒙缺,汉缺,五花八门,什么科甲正途异途,看得人眼花缭乱。
又遇到了清朝中后期,太平天国军功滥发功名,比如曾国藩手里的不记名监生名单,一大叠,随手赠给亲朋好友。
捐官又门户大开,没出身先捐监生,捐完监生,捐知县,通判,同知,知府,道台,还有钱还可以捐个二品顶戴。
但这都是只是头衔,不是实际职务,
实际职务,轮不到人,
杜凤治,中举人后苦等十几年,四五十才得到了一个知县,就这很多人一辈子也轮不上。
捐官捐到知府,但是最高做到知州。
很多官,一辈子就靠着委任某个差事,赚点外快,跟个乞丐差不多。
衙门捕快是著名强盗洗手后做,基本不抓真凶,喜用无辜人顶罪。
平日从不下乡办案,听任帮伙所为,往往以无辜人搪塞,且有指平人为匪拿押讹钱、得赃私释之事,实堪痛恨,二年以来十余名缉捕差从未闻拿获一真要犯。
家里的仆人科举连连得力,
官匪横行,走私贿赂,杀人放火,随处可见。
主打的就是一个礼崩乐坏。
广省村庄宗族械斗很上档次,还知道与时俱进,都用上火炮了。
广东是械斗严重的省份,械斗甚至使用火炮、抬枪等重火器,一些宗族、村庄在大规模械斗时还会聘请职业盗匪帮斗,“斗匪”焚屋、抢劫、掳人、杀伤人命、武力对抗弹压的弁兵、差勇也是常见的事。一旦发生大械斗,州县官都要会同武营前往弹压剿办。平息一场大械斗,相当于一次范围较小的清乡。
为了下乡收粮食,知县亲自带大炮轮船清乡,大炮是准备轰炸乡村和村民的。
仍以陈同所在的柳岗乡为例,同治九年二月,方耀清乡的主力来到柳岗乡附近,在方营办事的知县朱用孚还带来一艘装有大炮的火轮船。在此压力下,一直躲避的陈同,不得不同绅士陈炳坤(恩贡生)、陈忠爱(监生)来见杜凤治。杜对三人劝谕训饬了一番,便命陈同料理陈姓一族和外乡外村欠粮,不容分说,命陈立下限状,把欠粮完纳八成,按具结日期分批清缴,而且要求陈同“交匪”。
杜凤治人怪好的,说轰村活儿太糙了,应该烧村,“以服人心”。
杜凤治认为轰村的办法不行,建议朱用孚先焚烧“匪村”新寮,“以服人心,以吓匪人,而完粮亦心中生畏”。
如杜凤治亲自入村,到欠粮多、“无粮之田多”的绅士陈来远家,陈躲避,杜命在其门口标字“三日无人无粮,必焚其屋”。
广省强盗爱洗劫巡检司衙门,
杜凤治第一次任南海知县时就有两个巡检司衙署被盗匪抢劫。同治十年十月,盗贼二三十人,半夜明火持械入黄鼎司巡检署抢劫,把巡检李腾骧(雨村)一家所有财物、衣服抢去无遗,幸而官印未失。巡检本有缉捕之责,巡检署竟被盗贼抢劫,故不便禀报上司。杜凤治同广州知府商量把巡检署遭劫改报为“因窃失物”,为李腾骧保全了面子,使其免受严重处分。[275]次年十二月,江浦司巡检署又被劫,二十余盗匪夜里入署将巡检朱铣(北台)的财物、衣服搜劫一空。